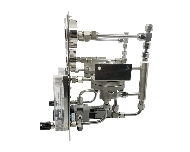1984年,鄧公考察寶鋼時有個題詞:掌握新技術,要善于學習更要善于創新。剛才突然意識到:這個題詞太英明了。
熟悉我的人都知道,我經常批判專家誤國。現在想來,這些磚家的問題就是學習太少。
我剛到寶鋼時提出一種說法:我在自己的專業里是博士,在其他專業卻連本科生都不如,應該從做小學生開始。而現代化企業涉及到多少專業?從管理到技術、從材料到工藝、從機械到控制、從煉鐵到軋鋼、從軟件到硬件、從領導到工人.....這里需要了解的知識太多了,可謂浩如煙海。寶鋼每做一個項目的時候,都會把不同專業和部門的人請來一起開會。就是為了彌補個人知識的不足。在企業里面久了,能學到太多學校里學不到的知識,尤其是實踐知識。
我經常談“路燈底下找鑰匙”這個寓言。它給我們的啟發是:人們看到的問題,往往受制于自己的視野。視野窄了,“關鍵”就會落入視野之外。這樣做事肯定失敗。在企業最大的收獲是視野廣了,把握問題的能力強了,知道問題的重點難點在哪里。而學術界對現代化工業的理解往往比較膚淺,總是自說自話地認定難點、又在自己的圈子里評價。我對十四五規劃的一個意見,就是看不到對學術界的改革,沒有打破傳統的圈子。按照耗散理論的觀點,封閉的圈子必然走向沒落。
其實,即便是在企業,學習也是很難的。
我做央企青聯委員時私下有個感覺:寶鋼是最好的央企之一。最近多次遇到寶鋼的老領導,我也談到:與其他國企相比,寶鋼是認真學習的典范,把日本人的許多東西學得很好。我估計,具有這種學習能力的企業,絕對不到十分之一。華為是其中之一,把IBM的一些東西學到手了。
如果說學好的企業不到十分之一,善于創新的企業又有多少呢?
我覺得,工業企業的創新應該是學習基礎上的創新。就像華為這樣。而現在很多企業是在沒有學習好的基礎上搞創新,這樣的創新不創也罷。
我發現,學習好的企業往往不善于創新。學習好又善于創新的企業,估計也不會超過十分之一。因為學習和創新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:學習要強調認真,創新又往往不能循規蹈矩。據說有一種現象:混得最好的同學,往往不是班里學習成績最好的。《從優秀到卓越》這本書有個觀點:優秀是卓越的大敵,說的也是這個道理。優秀的人往往追求確定性,而卓越的人則是在不確定性里尋找機會。大前研一先生甚至明確指出:學歷升高,創新能力變低。
我發現了一種現象:在某些單位或者部門,領導或者專家總體上往往“一代不如一代”。這種現象非常普遍。一個重要的原因是:先輩們往往是創業的一代,后面就是守成了。創業時代想的問題,后面就不想了,總是“蕭規曹隨”。視野也就窄了。正如孔子所言:取乎其上,得乎其中;取乎其中,得乎其下;取乎其下,則無所得矣。
我見很多人談論《相對論》時,經常說:牛頓認為時間是均勻的、認為力學定律是絕對真理。在我看來:說這種話的人自己沒有見識,總是用自己的眼界看牛頓。我在讀《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》時就發現:牛頓很認真地討論了這些定律和概念的邊界。在他的腦子中,這些結論都是可以改變的,只是當時沒有理由提出更復雜的理論。
學習者視野變窄,也是難以改變的。只有成為創新者,才能把視野擴大。但是,如前所述,創新者應該是學習基礎上的創新者,這樣的單位或者人不會多于1%。學習和創新不能兼顧,才是我們最大的問題。
孔子說:學而時習之,不亦說乎?學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則殆。在我看來:所謂的“學而時習之”,就是要把學習和實踐結合在一起;所謂的“學”與“思”,其實就是要把學習和創新思維結合在一起。
鄧公的要求高屋建瓴。但做到卻不容易:先要做到10%,在此基礎上再做到1%。
作者:郭朝暉(工學博士,教授級高工。企業研發一線工作20年;優也科技信息公司首席科學家;東北大學、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。國內知名智庫、走向智能研究院的發起人之一。原寶鋼研究院首席研究員)